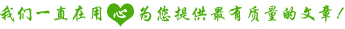人生常有一些美丽的邂逅,一个人,一处景,抑或一座城……到富阳,是一次计划外的旅行,在这之前,这个处于杭州西南角的富庶之地,一直没有进入我的视野,直到2017年春夏之交的某日,我因参加一个演讲方面的活动,意外发现了那一片被我忽略的风景。
初识富春
到达富阳时,已临近黄昏,雨刚停,屋檐上还挂着串串水珠,雨季的江南像经水煮的一般,到处湿盈盈的,环顾四周,见云雾弥漫,暮色渐起,入住的宾馆,在城外的福缘山上,名曰福缘山居,山居占地面积不大,但环境幽雅,几栋造型简约的楼宇,依山而建,错落有致地隐蔽在绿树丛林中,只露出橘红色鱼鳞瓦的屋顶,远远看去,像绿军装上的红领章,甚是显目。
走进客房,放下行李箱,第一件事,拉开厚厚的落地窗帘,我两眼一亮,顿时被眼前的景象震住了,宽大的落地窗,变成了巨大的画框,框住了一幅流动的画,画中一江似练,横贯东西,江上雾雨霏霏,烟波渺渺,不时有几只驳船缓缓驶过,远处青山逶迤,重重叠叠,好一幅青山秀水图,忽然想起,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富春江了,果然山色空濛,江水灵动。
遇见山水,就像遇见了自己,心中自有几分窃喜,感觉像偷吃了一顿饕餮大餐,特别的享受,一直想逃离都市的繁嚣,找一个能放逐心灵的地方,见到这片山水,就像找到了梭罗的“瓦尔顿湖”,心中有一种无法抑制的激动,于是像个疯子一样,冲下山来,驻足江边,感觉自己仿佛站在船上,随流水缓缓前行,习习的晚风吹乱了发丝,却涤荡了心脾,感觉肌骨清凉,万虑俱净,通体透明,所有的积郁都烟消云散。
夜晚,山上万籁俱寂,躺在床上,只听得见凉篷上“嘀嘀嗒嗒”的雨滴声,感觉人真空了一般,没有一丝杂念,连梦都没做成一个,第二天一早起来,赶紧拉开窗帘,见富春江处子一般静静地躺在窗前,呈现出与傍晚炯然不同的气韵。一向以为,最纯粹的美,就应是这般简洁、轻柔、自然、和谐的,这如诗如画的幻境,倒让人恍如梦中,我仿佛看到平静的江面上,一叶小舟,站着梁山伯与祝英台,正手拿折扇,唱着“青青荷叶清水塘,鸳鸯成对又成双”,从眼前漂过,那悠扬的越剧唱腔,一如富春江的水,清丽、透亮,拖着长长的水韵。
在接下来的几天活动中,我对富春江有了更多的了解,心中竟升起几分惭愧,平生也曾领略过不少名山大川,为何偏偏忽略了邻省的这片美丽山水呢?富春江是江南沃野的一泓清流,与我们皖南一脉相承,上游就是徽州的新安江,新安江与兰江汇合后,流入桐庐、富阳,称富春江,全长68公里,流经富阳就有52公里,横贯富阳全境,这一带山绕水生,水行山环,风光无限。
有山有水的地方必有灵性,自古以来,天下名士都喜欢到这里游历、隐居,东汉初年,名士严子陵乘一叶扁舟,悄然而来,便再也舍不得离开,在富春江畔搭了一个茅庐,坐在临江的石矶上钓起了鱼,过上了悠然自得的垂钓生活。元代末年,“元四家之首”黄公望,游历至此,发出了“富春山水终嘉遁”的感叹,随在此结庐隐居,画出千古名画《富春山居图》。清朝初年,画坛“四僧”之一的八大山人追寻大师仙踪来此,写下“比之黄一峰,家住富阳上”的佳句;民国初年,一代大师张大千也在原地写下“平生低首黄公望,结庐应须在富春”的诗句,可见富春江具有超强的磁场,“引无数英雄竞折腰”。富春江南岸的龙门古镇,聚居着三国东吴大帝孙权家族的后裔,据家谱记载,从三国时孙权到民国二十八年(1939年),孙氏已繁衍了65世,龙门古镇上的村民90%都是孙家的后代。富阳自古出才俊,有丰厚的文化土壤,孕育出郁达夫、罗隐、李育杭、王旭烽、麦家等现当代文学家,在富春江边的鹳山上,至今保留着郁达夫和兄长郁曼陀奉养母亲的松鹤别墅,郁达夫在早期的作品中多次描写家乡的山光水色和风土人情,他在自叙诗里写道:“家在严陵滩下住,秦时风物晋山川,碧桃三月花似锦,来往春江有钓船。”诗中描绘了富春江春天的美丽景色。郁达夫是一位作家,更是一名战士,他奔走在抗日最前线,以笔作筏,大声疾呼,最后被一双日本宪兵的手扼杀,为传承郁达夫精神,2009年富阳市政府以郁达夫之名设立了“郁达夫文学奖”,富阳也成为该奖的永久颁奖地。
这是一条文学的江,有着太多的故事,太浓的诗意,或者说,富春江本身就是一首诗。南朝吴均的《与宋元思书》对富春江的评价是:“风烟俱净,天山共色……奇山异水,天下独绝”,元代诗人吴桓写的“天下佳山水,古今推富春”大概最有名,流传了几百年,成了富春江的广告词,他俨然成为富春江的代言人。历代诗人游历至此,无不留下赞美的诗句,如果哪位诗人不吟咏几句,便辜负了这片绝世山水。唐代诗人吴融如绘画般地描绘了富春江的高颜值:“山迎水送入富春,一川如画晚晴新。云低远树帆来重,潮落寒沙鸟下频。”“天下有水亦有山,富春山水非人寰。长川不是春来绿,千峰倒影落其间。”唐代大诗人皎然笔下的富春江则别有神韵:“悠悠渺渺属寒波,故寺思归意若何。长忆孤洲二三月,春山偏爱富春多。”尤其是后一句,流传甚广,大凡大美之处,必出佳句名篇,文人骚客们难掩对这片青山绿水的偏爱,将最美最好的词句,都献给了富春江。浙江人民出版社曾出过一本《富春江名胜诗集》,摘录了自南北朝至清1500年间1003人,吟咏富春江山水的诗词,达两千多首,可谓蔚为大观。
不过,我以为,对富春江最好的艺术呈现,当属被称为天下第一画的《富春山居图》,来到富阳,我才知道,这里正是《富春山居图》的原创地。
大痴道人
时间倒回到600多年前,那个自号为“大痴道人”的黄公望,云游至富春江,便被这非人寰的山水攫去了魂魄,在这里他获得了性灵的安顿,找到了一个可以出大作品的地方,于是留了下来,开始了他晚年的艺术创作,《富阳县志》上说:黄公望“放浪江湖,爱富春山水之胜,泼墨画大岭山图,遂结庐于鸡笼山之筲箕泉,以终老焉”。晚年的黄公望将自己交给了富春江,这也是一次美丽的邂逅,一次画家与山水的激情拥抱,人与人需要心心相印,人与景需要神意相通,“山水有灵,亦当惊知己于千古矣”(东晋诗人袁山松语),遇上富春江,黄公望就像遇到了人生的知己,让他的晚年生活和艺术创作发生了质的飞跃,这是一种前世的机缘,可以说富春江成就了黄公望,黄公望也成就了富春江,如果没有富春江的灵山秀水,自然不会有《富春山居图》,同样,如果没有黄公望的描绘,富春江也枉有独绝天下的山水风光,在国人眼中,黄公望与《富春山居图》早已融为一体,黄公望就是《富春山居图》,《富春山居图》就是黄公望,这幅画奠定了他在中国绘画史上的特殊地位。
一个人一辈子能成就一件大事,也不枉来世走一遭,可人生是一场未知,没几个人一开始就知道自己这辈子该去追求什么,人生常常是错位的,你苦苦追求的,不一定会有结果,你不经意的倒会给你带来意外的收获,黄公望的前半生,基本上与绘画无关,他30多岁学画,50岁才专事山水绘画,创作《富春山居图》时,已是79岁高龄,在物质生活严重匮乏的古代,能活到这个岁数,还能画画,算是奇迹了,这才叫大器晚成。黄公望的最初人生目标,不在艺术,也不在山林,而在庙堂,年轻的黄公望一心一意走仕途,学而优则士是他的人生信条,也是古代大多数文人学子的人生信条,这本无可厚非,自古以来,哪个热血男儿的理想不是定国安邦平天下,有一番作为,黄公望更是年少时就对功名充满了幻想,可他一路上走得跌跌撞撞,最后落得遍体鳞伤,被踢出了体制外。
那个出身寒门姓陆名坚的小后生,幼年就失去了双亲,过继给永嘉黄乐做了养子,从此改名黄公望,字子久,好在黄乐家境富裕,黄公望也算是因祸得福,投了个好人家,黄家对这个养子寄于厚望,供其读书晓经,学音通律,大力培养,年少的黄公望聪明过人,是个学霸,一心渴望皇榜高中,大展凌云之志,可人生充满变数,命运偏不按你理想的路线走,年少气盛的他,遭遇了江山易帜,改朝换代的大动荡,大汉沦陷,元朝统治,废除科举,将文人进入仕途的通道斩断了,黄公望的仕途梦化为了碎片,估计这时他的心也碎了,饱读诗书,满腹经纶,大考小考考了无数次,一模二模“模”了无数遍,临考前却将高考制度取消了,真的比落榜还让人崩溃。不过文人气质浓厚的黄公望还是不死心,还是想当官,他苦苦等待,直到二十四、五岁才谋得一名书吏之职,大概相当于一个抄抄写写的基层公务员,他尽职尽责做到42岁,人生再次发生断裂,公元1314年,黄公望受上司张闾“以括田逼死九人”案牵连被捕入狱,出狱时,他已47岁,年近半百,华发丛生,人生还有什么指望呢?他心灰意冷,彻底死了当官的心,话说回来,也幸好黄公望无缘科举,仕途不畅,要不然中国历史上,就少了个大画家,多了个官僚(说不定还是个贪官),哪会有那幅千古名画呢?
脱离了主流社会,黄公望出家做了道士,开始了他下半程的游历人生,中国历代文人大体如此,在经历了几度摧残几多失意后,归隐田园,寄情山水,“归去来兮,田园将芜湖不归”。据历史记载,黄公望入的是全真道,号“大痴道人”,全真道为儒、释、道三教合一,入教后的黄公望修炼得仙风道骨,越发看破了红尘,他在松花江畔以卖卜维生,不过一个公务员,竟在江湖上干起了卜卦算命的营生,也是一种悲催,但这种放浪形骸的生活,让他获得了身心的自由,“行到水穷处,坐看云起时”,闲云野鹤般的生活,无疑是适合搞艺术创作的,退一步海阔天空,在江湖,他找到了新的目标,官场的失意,反倒刺激了他的艺术神经,他将后半生的精力投入到了绘画创作中。不知黄公望自号“大痴”,有何深意,是大喜大悲后的顿悟?还是大空大寂后的超脱?或是痴心不改、至死不悔的痴绝。想来历朝历代的大文豪哪个不是痴绝的呢?不到痴绝处,怎到物我两忘的大境界?何来流传千古的大作品?典型的要属曹雪芹,“满纸荒唐言,一把心酸泪,都云作者痴,谁解其中味”,相信黄公望的人生体味一定不比曹公少,否则他也画不出那超然独绝的画,孟子曰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,必先苦其心志,劳其筋骨,饿其体肤,空乏其身,行指乱其所为,所以动心忍性,曾益其所不能。”这几乎是一条颠簸不破的真理,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,真正的艺术作品都是用生命创作出来的,对黄公望来说,前半生是他的人生历炼,是铺垫,是为创作打下的基础,如果没有前半生的磕磕绊绊,哪能体味出人生的真谛,获得情感的升华,也必定没有晚年的《富春山居图》。曾读过一个写作的人的这样一段话,他说一种有缺陷的生活也许会更吸引他,适度的窘迫,有疼痛感的童年,短暂的贫困,不景气的外貌等等,只有当生命被置于这些缺陷当中时,生活才变得真实而有质感,作家如此,画家也当如此。艺术是失败催生的,更是苦难酿造的,往往要承受生命的煎熬,付出惨烈的代价,翻遍历代文豪的作品,似乎有这样的规律,那些惊天地、泣鬼神的作品,大都在不得志的时候创作的,屈原遭流放才会向天发问,写下忧国忧民的《离骚》,李白被赶出皇宫,才有了更多吞天吐地般的豪放诗句,成为“谪仙人”,白居易贬到江州当司马才写出《琵琶行》,范仲淹、苏轼、辛弃疾无不是被贬失落时,写下那些千古名篇,杜甫就更不用说了,一辈子穷困潦倒,却成了诗圣,还有那位唐后主李煜,当朝时过的是“车如流水马如龙,花月正春风”的日子,词作绮丽风华,奢靡之极,当他失去江山,沦为阶下囚后,才写出那些国破家亡的悲伤体验,成为一位千古词人。一个人太顺利、太完美、太得势,大概是写不出什么惊世之作的,只有当他不顺利、不完美、不得志时才会有更多的感悟、不平和喜怒哀乐,所谓“愤怒出诗人”正是这个道理。
只不过晚年的黄公望全无了早年的“愤怒”,青山绿水抚平了他内心的不平,他放下了一切尘缘,如一江波澜不惊的水,容得下万倾碧波,隐居在筲箕泉的黄公望,“卧青心,望白云”,朝看山色之空濛,暮观烟云之变幻,超然世外,像一只修道成仙的松鹤,他的全真教修炼,不仅是一种性情的修炼,也是一种艺术的修炼,让他的绘画技艺在晚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,黄公望被称为“元四家”之首,可见是个大师级的画家了。
雨访庙山坞
活动期间,主办方安排参观黄公望隐居地,正合我心意,能追随大痴的足迹,寻访大痴隐居地,体验“富春山水终嘉遁”的意境,也不枉此行了。
雨一直痴迷地下,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,江南的雨季,就是这么任性,感觉山川沃野都是泡在水里的,还有恣肆的风,夹着雨,一阵又一阵地横扫,吹得伞都翻了过来,到达黄公望隐居地时,浑身上下都能拧出水来。
黄公望隐居地——庙山坞,即现在的富阳森林公园,这里山虽不高,但植被繁茂,森林覆盖率极高,庙山坞因庙而得名,宋时这里有净因院,苏东坡等文人雅士都曾来此吟游。这一带有许多美丽的传说,比如说神仙赤松子曾驾鹤经过富春江畔,鹤鸣而仙气萦绕,至今留下白鹤桥、白鹤墩等遗址,还说王母娘娘的侍女董双成也在这一带栖居活动,这里是仙女来过的地方。我以为,黄公望到此隐居除了山水所引,大概也因这里人文深厚,况且黄公望本人就是个传说,在黄公望纪念馆入口处,有一首民谣饶有趣味,“从前,富春江边有个白鹤墩,白鹤墩边有个庙山坞,庙山坞里有个小洞天,小洞天里有个南楼,南楼里有个仙风道骨的老人,老人画了《富春山居图》”
雨中的庙山坞水雾氤氲,峰峦滴翠,郁郁葱葱的密林间,松涛阵阵,溪流淙淙,走在通往坞底的山道上,仿佛找到了原始的自己。
资料上说:庙山坞的溪流发源于坞底的如意尖与野山头两峰之间,那有一个山头,形状象一只反扣的筲箕,溪流经黄公望结庐处小洞天,在山谷中汇积成若干水潭,在小洞天外不远处的水潭,俗称“筲箕泉”,原来“筲箕泉”是这么来的。而“小洞天”是黄公望自己起的室名,出自黄公望一幅画的题款,他在《秋山招隐图轴》的题记中描述:“此富春山之别径也,予向构一堂于其间,每当春秋时焚香煮茗,游焉息焉。当晨岚夕照,月户雨窗,或登眺,或凭栏,不知身世在尘寰矣。额曰“小洞天”。这段描述正是他超然世外隐居的生活写照。
“小洞天”藏在竹海深处,途经“庙坞竹径”,是进入“小洞天”的前奏,那一片竹林幽深、挺拔,遮天蔽日,让人生敬,中国人对竹子一向情有独钟,竹子象征君子之道,竹称君子,君子如竹,不柔不刚,高风亮节,竹子的精神与中国士大夫的精神十分契合,“门对千竿竹,家藏万卷书。”也是中国文人向往的精神财富。苏东坡当年曾在此留下《净因院竹轩》一诗:“轩前有竹百余竿,节节浑如玳瑁斑。雨过风清谈般若,琅玕声撼半窗寒。”300年后黄公望也和了一首《题苏东坡竹》:“一片湘云湿未干,春风吹下玉琅玕。强扶残醉挥吟笔,帘帐萧萧翠雨寒。”这是两位大师跨越时空的对话,这片竹林放在这里,可是别有意味。
来到“小洞天”,见柴门半开,似有虚以待客之意,站在苔痕斑驳的院内,感觉进了一座农家客栈,几间仿古的茅屋,木质结构,古朴肃穆,挂着“小洞天”牌匾的是黄公望的起居室,室内陈设简单,中堂挂着黄公望画像,画中的黄公望手持拐杖,仙气飘飘,身边一只白鹤悄然而立,两边的对联感觉有浩然之气,“大痴胸次多丘壑,巨颖人间识凤麟”,胸有丘壑,既是画家的必备,也是人生的必需,没有丘壑,如何描摹山川大地,没有巨颖如何识得人间沧桑,这是对黄老先生精湛技艺和高尚人格的高度赞誉。
院前方,下几级台阶,便是临塘而立的“南楼”,先生的创作室,室内清气飘然,墙上挂着山水画,桌上放着毛笔砚台……我在画室里转悠,像个寻古问道的考古先生,那一桌一椅,一笔一砚,唤起我对古时的遥想,感觉自己玩了把穿越,看到80高龄的一代大师坐在南楼的窗前,饱醮生命之情,一笔笔勾勒、描摹、皴染……
清代大画家石涛有句名言,叫“搜尽奇峰打草稿”,而黄公望早在几百年前就这么做了,他天天背着行囊,揣着画笔,游走在富春江的青山绿水间,见到好的景色就坐在江边的石头上,潜心观察,现场写生,他把富春江两岸的一山一水,一草一木都记在心头,画下了大量的创作素材,黄公望撰有《写山水诀》,为山水画创作的经验之谈,他说,“或画山水一幅。先立题目。然后着笔。若无题目。便不成画,更要记春夏秋冬景色。春则万物发生。夏则树木繁冗。秋则万象肃杀。冬则烟云黯淡。天色模糊。能画此者为上矣。”《富春山居图》正是搜集了富春江两岸的千丘万壑,溪流河水,沙洲垂钓等自然景色,经过精心构思,细细揣摩,才创作出来的。据考证,图中描绘的景色也是富阳境内风光最佳的一段,画中的山形、水势、沙洲、气貌都能在富阳城东株林坞和庙山坞一带找到对应。
公元1350年,黄公望历时六七年完成了描写富春江两岸秋景的《富春山居图》,这是幅山水长卷,画面上:丘壑起伏,连绵不断,远山近水,层次分明,沙洲平畴,疏密有度,渔人泛舟,悠闲生趣,山石树木,参差不齐,山以长披麻皴为主,墨线疏松,浓淡粗细相照,色彩上,用淡赭色渲染秋意,呈现出生动自然的明媚色调。由于画卷有3丈多长,展开让人应接不暇,有咫尺千里之感。
六、七年,可是二千多个日日夜夜啊!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艺术长跑,可谓十年磨一剑,郑板桥有两句诗:“四十年来画竹枝,日间挥洒夜间思”,黄公望大概就是这么创作的吧!
山水画的最高境界是寂寞,庙山坞空山无人,小洞天寂寥无声,黄公望静自太古,时间仿佛在这里凝固了,只有他跳动的心如铜壶滴漏,那记忆深处的山川、河流、浅滩、沙洲,在他的脑海里幻化成图像,似涓涓溪水从笔墨间缓缓流出,与其说在画画,不如说在用笔墨书写人生,“泻”出心胸,表达漫长人生的妙悟。一笔笔都是如泣如诉,一点点都是低吟浅唱,不经历漫长的人生历炼,没有入世又出世的大彻大悟,如何画出高古、寂寞的禅意,艺术,不是技艺,它是艺术家表达性灵的工具,《富春山居图》意境高远,画风简洁,就像一个睿智的老人,平和、宁静,表现出绚烂之极,归于平淡的禅道哲学,但这种平淡不是淡而无味的平淡,而是脱离了尘世的静穆,平淡中有苍莽和智慧,后人称之“峰峦连厚,草木华滋”“一丘一壑写高古”。
黄公望一生画作不多,存世之作只有《富春山居图》、《天池石壁》、《九峰雪霁》、《丹崖玉树图》等屈指可数的几幅作品,《富春山居图》是其生命中的最后一件作品,也是其巅峰之作,是生命的绝唱,《芥子园画传》说:黄公望皴,仿虞山石面,色善用赭石,浅浅施之,有时再以赭笔钩出大概。这大概就是他首创的“浅绛”法。我不懂作画,无法从创作技巧上给予准确的分析,但我觉得,起码太年轻的人画不出,太富足的人画不出,甚至太肥胖的人都画不出,只有清心寡欲,洗尽铅华,悟透了人生哲学的人才能画得出,这不是一种技巧的呈现,而是一种修为的升华。写作讲究语境,作画讲究笔意,画得像不难,难的是画出太古的意韵,画出岁月的风蚀,生命的境界。范仲淹激赞严子陵的话,亦适合评价黄公望:云山苍苍,江水泱泱,先生之风,山高水长。佛家参禅讲究三重境界,即“见山是山,见水是水;见山不是山,见水不是水;见山还是山,见水还是水”这也是艺术创作的三个境界,尤其是第三个境界为彻悟之境,黄公望正是追求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,才会有这画中之“兰亭”。
一幅画的命运
一幅画的命运,大体相当于一个人的命运,世间名画佳作千千万,可没有哪幅像《富春山居图》这样命运多舛,不仅仿作无数,真假难辨,还被人抢,被人盗,险遭火劫,它的悲欢离合的故事甚至可以写一部长篇小说。
黄公望在《写山水诀》中说,作画大要,去邪、甜、俗、赖四字,这是他的作画之道,也是为人之道,可天下又有几人能悟得此道呢?
世人都道神仙好,惟有功名忘不了……
世人都道神仙好,惟有金钱忘不了……
曹雪芹在《红楼梦》开篇就借跛足道人之口唱出了《好了歌》,道出了人生百态,揭露人们被各种欲念所蒙蔽,看不破,悟不透,无不在金钱、名利、欲望上你争我夺,鱼死网破,《富春山居图》数百年来在民间经历的“巧取豪夺”,或许就是个例证。
《富春山居图》是黄公望为同道的无用师弟画的,画上题跋如是写:“至正七年,仆归富春山居,无用师偕往,暇日于南楼援笔写成此卷,兴之所至,不觉亹亹”,“亹亹”是勤勉不倦的意思,这段话描述了他作画的时间、地点和当时的心情,是兴之所至,不知不觉画了很长时间。这无用师弟叫郑樗,俩人关系不错,常在一起品茗对弈,82岁的黄公望,兑现承诺,将呕心沥血绘成的《富春山居图》赠与无用师弟,不久便驾鹤西去,成为一个永恒的传说。《富春山居图》无疑是中国山水画的极品,但黄公望生前却没有因这幅画而得到什么荣华富贵,他得到的只是身后名,第一位受益者是无用师弟,这样一幅不同寻常的山水长卷,他怎能不担心将来的命运,所以让黄老先生“先书无用本号”,早早写下他的名字,明确归他所有,黄大师也精于卜卦,甚至在画未完成时就写下了尾跋:“无用过虑有巧取豪(夺)者,俾先识卷末,庶使知其成就之难也。”他想让世人先从画卷的结束部分看起,了解创作这幅画的艰难,遗憾的是后人却不理解大师的良苦用心。好的东西,人人都想占为已有,无用师弟是个吃白搭的,没花一个银子就得到了这件宝贝,当然这是友谊的象征,可他不久也离开了人世,他的后人却将画卖掉了,从此流落民间,下落成迷,估计没人搞得清《富春山居图》曾被多少人收藏过,它在民间像接鼓传花似的传来传去,到了明成化年间,大画家沈周收藏了此画,他收藏的时间不长,可留下的故事最多,沈周被称为“明四家”之首,一生专注于诗文书画,据说是唐伯虎的老师,沈周不仅画画得好,还爱收藏,画与人一样,也需要投缘,《富春山居图》传到沈周手上,算是找到了知已,沈周对此画百般推崇,视若珍宝,将它挂在墙上,反复欣赏临摹,看到画上没有名人题跋,他便请朋友题跋,谁知被朋友的儿子偷走卖掉,还佯说被盗,即谓“巧取”,沈周像丢了爱妾一般痛惜不已,可生性厚道的他,却无从追究。之后沈周一次在街上的画摊上又见到了《富春山居图》,他激动万分,仿佛旧人重现,忙跑回家筹钱,可等他回来时,画已被人买走,再一次与爱妾失之交臂,他捶胸顿足,悲恸不已,后来竟凭记忆背摹了一幅,就是著名的《仿富春山居图》,沈版的图,与黄版的图虽有出入,但起码解了他的相思之苦,得到精神上的安慰,他在画上题曰:“思之不忘,乃以意貌之,物远失真,临纸偶然”,爱画爱到这个地步,也是足够痴迷了,真乃又一“大痴”,后来他的好朋友樊舜举高价购得此画,当沈周在朋友家看到《富春山居图》时,感慨万千,可失去了就永远地失去了,已无再次拥有的可能,他在画上题下了自己拥画失画的故事,还慷慨地将自己的仿作送给了友人,传为佳话。多年后,明代又一书画大家董其昌收藏了此画,也是万分欣赏,说“子久画冠元四家……如富春山卷,其神韵超逸,体备众法,脱化浑融,不落畦径。”并对照临摹,董其昌晚年因生活拮据,将此画典质给了吴正治,却再也没有赎回。
公元1650年《富春山居图》落到吴家第三代吴洪裕手中,这个吴家三公子也是个画痴,而且痴得走火入魔,他爱极了此画,终日不离身,到死竟要把画带到来生去,他在弥留之际要家人烧画陪葬,就在画被点燃的那一刻,其侄吴静庵“疾趋焚所,起红炉而出之”,侄子冲出来,将画从火中抢出,偷梁换柱烧了另一幅画,此画才得救,可画卷已烧出几个洞,断成两段,一长一短,吴家后代将小段烧焦部分揭下,重新装裱,正好有一山一水一丘一壑,几乎看不出裁剪过的痕迹,从此,小段部分被称为《富春山居图•剩山图》,大段部分被称为《富春山居图•无用师卷》
《无用师卷》真迹于1746年(乾隆十一年)被征入宫,不过令人啼笑皆非的是,乾隆皇帝却闹了个乌龙,原来在此前一年即1745年,乾隆已得到了一张《无用师卷》,爱不释手,珍藏身边,反复把玩,并在空白处赋诗题词,加盖了十几个方印,可这张图却不是真迹,是明末文人临摹的仿作,人称《子明卷》,一代明君楞生生被骗,将仿品当真迹,第二年当真迹《无用师卷》来到他面前时,他反而说是假的,不过觉得也画得好,留在了宫中,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被书画鉴定大师徐邦达鉴定出来,予以纠正。《无用师卷》在宫中安放了187年,1933年日本鬼子攻占了山海关,《无用师卷》随故宫博物院藏品转移,历经辗转,抗战结束后,运抵南京,又于1948年底,随国民党退却,被运往台湾,现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馆。而前半段《剩山图》一直流落民间,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才被浙江省博物馆高价收藏,成为该馆的镇馆之宝,一湾浅浅的海峡将一画分隔两岸,从此,“我在这头/大陆在那头”。
这幅画坎坷沧桑的传奇经历,像极了我们多难的民族,“我希望两幅画什么时候能合成一幅画,画是如此,人何以堪”,2010年3月,在全国“两会”的记者招待会上,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说的这句话,激起了千层浪。不负山水,不负公望,两岸有识之士,以此为契机,开启了一段艰难的画卷合一的征程。于是600多年后,《富春山居图》又演绎了一段新的传奇故事,而且比几百年前更加动人心魄,2011年5月,《富春山居图•剩山图》穿越了历史,跨越了海峡,来到了宝岛台湾,6月1日,“山水合璧——黄公望与《富春山居图》特展”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盛大开幕,饱经沧桑的“中国山水第一神画”终于在遭火劫360年,分隔海峡两岸60年后合璧展出,画因人而断裂,画又因人而合璧,这历史性的“山水合璧”,其实早已超越了书画艺术的范畴,成为两岸炎黄子孙的“心灵之约”。
台湾著名词人方文山,特地为《富春山居图》的合璧展出创作了主题曲《山水合璧》
落笔从容起山峦
你浅绛色引峰回百百转
我不由轻叹初秋微凉
景萧萧却委婉
富春山居隐山岚
山坳处结庐人家尽遮半
……
历史在纸上回荡
我看山水合璧历历沧桑
故事轮回了几场
听小桥水又一弯
这首词荡漾着古典怀旧的意韵,带着浓浓的“方”式风格,既是词更像是诗,有着浓烈的画面感,方文山就一奇才,黄公望是用笔作画,方文山是用词作画,这首歌由费玉清和张靓颖唱出,该是怎样的清澈空灵,直灌人心啊!
在黄公望纪念馆,我目睹了三幅不同版本的《富春山居图》,展厅两边的柜子里展示的分别是清乾隆皇帝误为真迹的《子明卷》和沈周背摹的《仿富春山居图》,展厅正中央的展柜中陈列的是高仿品《富春山居图》“原画”,将《富春山居中图》的《剩山图》和《无用师卷》完整地呈现出来。
“今日已无黄子久,谁人能画富春山?”相信终会有一天,两岸的炎黄子孙,定会让这幅旷世名画永远地合璧在一起。
【审核人:站长】